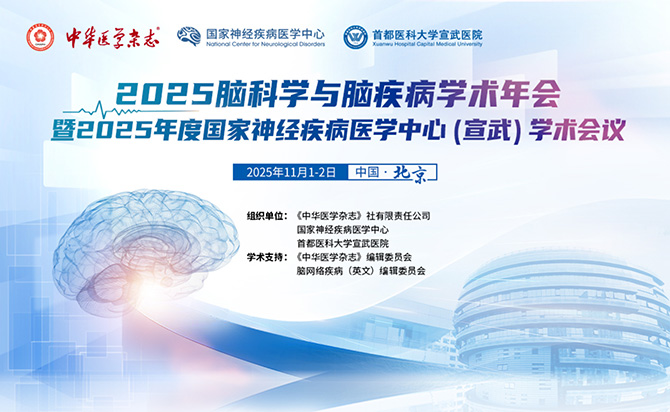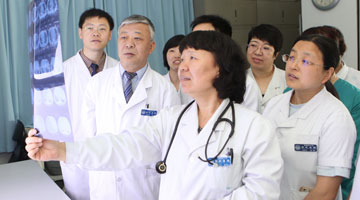科室新闻
马妍:我与搭桥手术的二十年 #CMOSS-FU研究登顶JAMA

初入神外:与搭桥手术结缘
2025,是干神经外科的第20个年头,也是和搭桥手术结下不解之缘的第20年。
2005年的冬天,一个协和医大八年制即将毕业的女生,站在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凌锋教授的办公室里,手攥着简历,正紧张地盯着手术室中传来的实时视频。屏幕里播放的,正是一台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手术。当凌导忙完回到办公室,看我认真看手术的样子,微笑着说:以后这种手术,你来做怎么样?攥着简历的手有些冒汗,我有点尴尬地笑笑,没有敢接话。
当我如愿加入宣武神外团队,踏踏实实地做起“24小时外科住院医生”的时候,从腰穿、脑室穿刺、气管切开、深静脉穿刺应接不暇的ICU开始做起,到肿瘤组各种肿瘤诊断、鉴别诊断、术后处理以及练习开关颅,工作不到一年,我就被推到了“住院总”的岗位上。那个时候,住院总面临最多的急诊是急性脑血管病,各种各样的脑出血、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急诊开关颅、都需要住院总的组织与带领。隔天一个24小时班,而下24小时班的那天,需要参与神经外科的各种择期手术。对于八年制毕业的学生来说,读书时真正动手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我总是格外珍惜这个机会,从不拒绝任何一个开关颅的“邀请”。这其中,也包括李萌主任的搭桥手术。也许是凌导善意的安排,也许是我认真学习的模样给李主任留下了“靠谱”的印象,他总是让我坐在“一助”的位置上,在助手镜下参与完整的手术过程,这对于刚毕业一年多的住院医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殊荣”。术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手滴水冲洗术野,一手拿显微吸引器吸走术野的积水和血,在保持术野清爽的同时,两手要稳稳地不产生一丝不必要的晃动,以免对10-0的针线缝合产生扰动。双眼在镜下持续关注着针线的动态,手眼协调,精神高度集中。整个吻合过程很少听到李主任和我说话,而吻合结束后,他总是会讲起自己做外科医生的经历,诙谐又有趣。下了手术他会戴起花镜,坐在护士站认真写着每一份手术记录,并换成红蓝铅笔画下手术的示意图。而我,总在忙完所有收尾工作之后,打开他写的手术记录,看着那些图,再反复琢磨琢磨。再后来,李萌主任会借给我看Yasargil教授的《显微神经外科学》,里面精美的绘图、对于显微手术技术的观点,令人叹为观止;有时也会看似漫不经心的“扔给”我一些关于搭桥手术的英文文献,引导我开始接触慢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各种细节。渐渐地,有问题我也敢“斗胆”向李主任请教,当然大多是一些非常low的“低级”问题,他也会偶尔开玩笑说“你可是协和的大博士毕业”之类的话,当慢慢的问题多起来且专业起来的时候,有一天,他很郑重地和我说,“凌导有个博士后叫焦力群,他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认识和理解都很深,如果有他讲课,你一定去听听。”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李萌主任(左)
转向科研:循证医学的启蒙与挑战
那个时候,正是国际上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焦主任邀请华西医院循证医学中心在宣武举办了一次神经外科循证医学学习班,在此鼓励下,我完成了首篇颈动脉狭窄支架与剥脱治疗的Meta分析,并发表在《中国脑血管病杂志》上,算是开始系统接触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循证医学知识。GCP、RCT、Meta、DSMB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熟悉的字眼,在那时的神经外科医生心目中,依旧是相对陌生的存在。在缪中荣主任和焦主任带领的缺血组轮转,第一次穿铅衣上台做造影前,焦主任给我强调了所有导丝导管的操作细节,还特意安排了优秀的许丽华姐姐带我上台。那时缺血组开刀的手术日非常少,内膜剥脱手术常常接台又做到很晚,焦主任总是很暖心地为所有加班的人订饭。他们把组里所有上搭桥手术的机会都留给了我,也把这些病人的管理全流程托付给了我,在完整管理一个个搭桥手术病人的过程中,让我对慢性闭塞性脑血管病的病理生理以及围手术期处理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彼时的中国,搭桥手术被认为是显微神经外科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手术,能独立完成颅内血管显微吻合的医生资源稀缺。而我在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团队里,经过Yasargil显微外科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经过所有前辈们的悉心培养,在工作后不到五年,就可以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完成脑血管搭桥了。还记得自己首例搭桥病人术后复查造影通畅,恰好被缪主任看到,他比我还要高兴,甚至还因此请组里吃了晚饭。
在技术的学习曲线达到稳定后,恰逢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申报。缺血组已经可以成熟的开展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各项外科及介入治疗工作,时年工作刚满五年的我和高鹏一起,在焦主任的带领下,参与了这次国家十二五项目的课题申报。现在回头想想,应该也是我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看了多少文献、查阅了多少资料、改过多少版本的标书已经记不起来了,唯一还记忆犹新的是获得中标消息的那个晚上,我还在值着夜班。我从病房走廊的这头走到那头,仿佛要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这并不是梦。然而梦想与现实总是差别很大,我们可以模仿着欧美RCT的标书申请、临床研究注册,却没有想到,在视手术为“最后救命稻草” 的中国病人中推行“随机分组”有多么难。因为按方案需要随访很长时间,为了确保每个病人的“粘性”与“依从性”,所有入组病人都是我们三人谈话签字从头至尾跟进的,每个病人都设计制作了专属的随访登记本,时至今日仍有病人拿着那精美的小册子回来复查,并和我说:这个册子和“身份证”一样重要。今年五一期间仍有当年入组的病人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侄女癫痫了,能不能帮忙给挂号看病。我们像珍惜“绝世珍宝”一样“宠溺”每一个愿意加入研究的患者,无形中也在患者中树立了“专业”、“用心”的形象,在民间普及了积极科学参与临床研究的理念。比对患者教育更难的,是获得多中心神外大同行对RCT研究的认可。在那个时候,在神经外科医生中推行“随机”、“标准化操作流程”、“随访”更是非常困难。外科医生更习惯于对技术精益求精,“有手术做”、“做完挺好就行”,对于手术前的评估、麻醉的配合以及术后的观察随访尚未形成更完备的理念体系。那时,很多分中心的PI都已是业界大佬,与还只是一个“小主治”的我似乎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外科工作里的“经验习惯”想被“标准流程”替代,需要更多耐心的交流与磨合。这对于一个“社恐”的我来说,也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我需要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引导各个分中心的PI从内心接受方案、遵守流程。面对诸多“大神级”的前辈,反复交流时“诚惶诚恐”的忐忑心态肯定是有的,但给我更多勇气的是对慢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病理生理学基础的扎实掌握,以及对既往各项临床研究结果的深度熟悉与解读,让我在与他们交流时,平添了几分专业与自信。

临床深耕:管理能力与技术边界的突破
第一个十年过得很快,精进脑血管搭桥技术与开始从事临床研究,就这样进入到我的职业生涯中来,并顺理成章的成为工作的主线。一个懵懵懂懂“有点轴”的姑娘,以搭桥给予的执着与自信,精力充沛又乐此不疲的精神,赢得了各个分中心PI的理解与支持,以中国神经外科医生更加专业科学的形象,共同书写着属于CMOSS研究的历史。
第二个十年开始,神经外科缺血组在全院率先开展全组临床路径化管理,CMOSS研究流程被写入临床路径,向所有做搭桥手术的患者推广。我加入缺血组,从主治做起,弥补除搭桥手术外其它缺血性脑血管病外科治疗方面的短板。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可以带着一大帮人从病房的一头查到另一头,是一件非常光鲜的事;但就专业人士来看,这是一件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事,每一个跟随的大夫大概只需要管1-2个病人,但被簇拥“核心”的那个人,需要管的是整组所有的病人。缺血组患者大都是老年人,合并症多,病史复杂,“核心人”需要记住每一个病人的情况特征,把控每一个细节与变化,做出最及时有效的决定与处理。而这件事,在我们中心,每天雷打不动的早晚各有一次,每周有12次,一直坚持至今。而那个“核心人”,就是我。于是我迅速练就了超强的“联想型”记忆能力,能凭着管床医生给予的一点线索迅速“输出”对应病人的所有症状体征体格检查化验与影像学,时至今日依然让组里的年轻医生叹为观止。在临床路径的指导下,缺血组很快承担了整个神经外科最快的周转效率与病人量,如何在相对单纯高效的治疗中,让检查评估相对复杂的搭桥手术也不掉队拖后腿,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整合评估资源,尽量“一站式”检查提高效率,又面临着和辅助科室的新协作。平等双赢、互相尊重是合作的前提,在焦主任和卢洁主任“由来已久”的“长期友谊”基础上,放射科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开放与支持,让搭桥手术的平均住院日缩短了近三分之一,在临床管理上更加紧凑与科学。我的临床工作越来越多,接触到的新的治疗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各种介入材料与技术日新月异,慢性闭塞性脑血管病中很多可以通过复合手术或者介入再通恢复血流,搭桥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少,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第二个十年,是搭桥手术比例在我手中“越来越少”的十年,却是个人临床技能与管理技能获得全面提升的十年。搭桥依然是我最享受的手术,可以静静地在显微镜下心无旁骛;也依然是我最牵挂的手术,可以“润物无声”抑或“瞬息万变”。
研究涅槃:从阴性结果到十年随访的逆转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包括当时做临床研究的激情。对于CMOSS研究的推进慢慢被我巨大的临床工作洪流裹挟,很快就消失不见。好在研究进入正轨,有一众已经“志同道合”的各分中心PI支持,最终按计划完成了入组。2019年底,我到瑞士苏黎世参加Bypass2020峰会,当时CMOSS研究已经结束所有患者2年随访,但数据被我以“各种忙”的理由搁置了近一年的时间。与会期间不断有各国学者提起CMOSS研究并表达着期待结果的公布,说实话,我是带着深深的愧疚与自责的心态回来的。在回国的飞机上就想好,一定要推进最后的数据分析工作了--尽管这是一个临床医生最不擅长的工作。回国后,疫情就来了,作为外科医生,虽然临床工作量减少了,但是有大量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去承担解决,当然也有了更多时间思考数据分析工作应该如何推进。感谢协和王韬师弟的加入,以他在临床研究数据分析方面卓越的经验,一步步帮我把最后的工作推进完成。感谢武阳丰老师、汪海波老师专业严谨的精神、高效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CMOSS把最好的结果呈现给世人—尽管2年随访,复合终点仍然是阴性结果。
后面的经过大家应该都了解了,JAMA投稿返修接收都非常顺利,十几年的工作,貌似是应该有个“圆满”的收尾了。但在30天的安全性终点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到,中国神经外科医生以精湛的技术、严谨科学的围手术期管理方式,将搭桥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降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水平。只有2年的随访时间,对于这种相对高风险的治疗来说,尚不足以体现出明显的获益,那如果我们再延长随访时间,结果会不会不同呢?
CMOSS-FU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此时,距离第一个病人入组,已经满10年。我从主治到主诊,“小兵”已成长为“老同志”。再次启动对330例患者的随访,尽量全面的获取到所有的临床影像信息,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感谢每个入组的患者,当年无论是否手术,均认可并配合我们持之以恒的跟进与随访;感谢赵院为首的医院领导给予了非常全面的支持,感谢协和八年制刘德临师妹以及我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孙心仪,两个细致女生很快温习了既往的数据与结果,设计出最简洁的CRF,组织协调新一轮的多中心数据随访工作。她们应该像我当年一样,在数据收集工作中碰了很多壁,当她们向我求助时,我会及时帮她们联系分中心PI--这“帮“近10余年结下深厚“并肩作战”友情的同道们早已换用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面对新的研究,第一时间安排最得力有效的方式帮助团队化解难题。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刘德临医生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孙心仪医生(右)
CMOSS-FU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是属于拥有更加科学理念与方法的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速度,也是属于逐渐接纳临床研究并积极参与研究的中国患者的速度。这一次,我们获得了阳性结果。当汪老师告诉我们这个结果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的是CMOSS研究的Logo要变一变了,桥血管为大脑注入了新鲜血液使长期随访看到了相对满意的效果,缺血区的“无色”要变成温柔明媚的“粉色”了;搭桥手术作为显微神经外科的经典手术,在中国新一代神经外科医生的手下,理应焕发出新的光彩。

logo设计者:宣武医院介入放射科 张白茹
二十年回望:站在山顶看世界
今年,是我做神经外科医生满20年。CMOSS系列研究再次把搭桥手术送到循证医学金字塔的塔尖。常常想起那句话:爬到山顶,不是为了世界能看到你,而是你能看到世界。感谢搭桥手术培养了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缺血性脑血管病治疗的大门。时至今日,已呈现出一副愈发多元化治疗的态势,一个新的世界之门已经打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留给下一个十年。
作者简介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现任Yasargil显微外科训练中心主任,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苏长保教授指导下获得神经外科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工作,尤其在脑动脉血管狭窄、闭塞性病变的搭桥手术和复合手术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作为主要研究者主持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和北京市科委等课题,参与“十三五”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十余篇,主编著作1部,主译2部,国家专利4项。